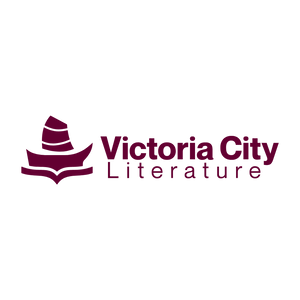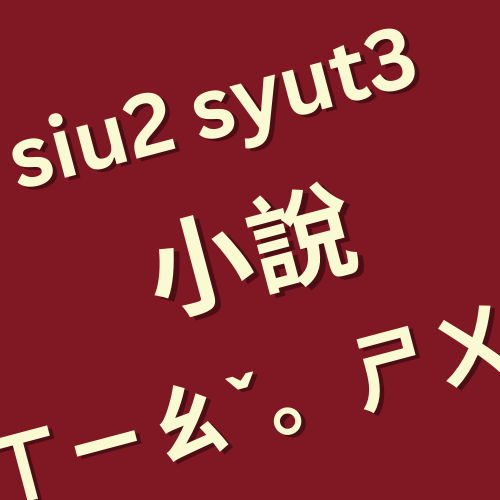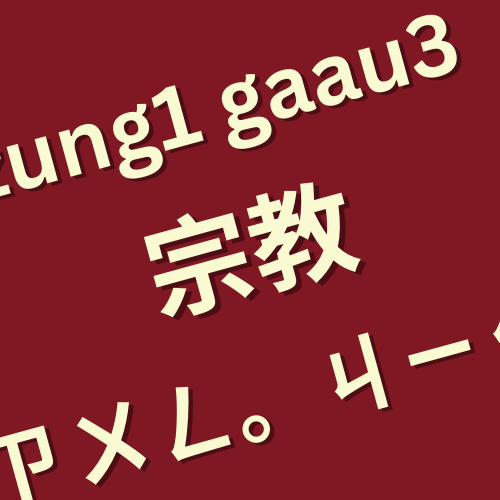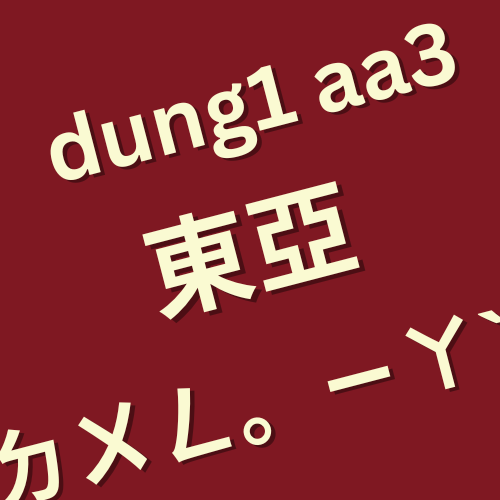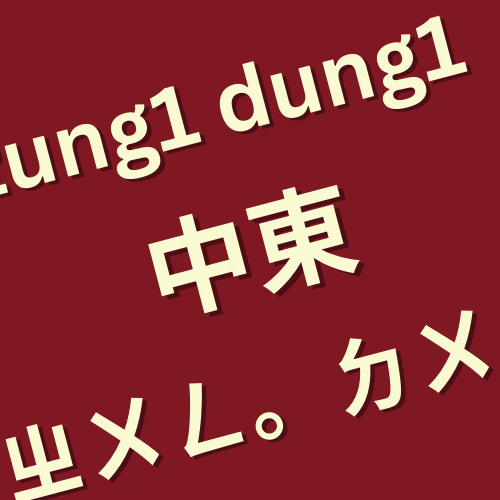渠成文化
革後餘生:從牛津大學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 徐友漁
革後餘生:從牛津大學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 徐友漁
無法載入取貨服務供應情況
說明
內容簡介
「雖然我深知,相較於滾滾歷史巨流,我所發出的聲音微不足道,甚至整個知識界的喧嘩爭鳴也可能被後人視為杯水風波;然而,我想強調,每個個人的努力與經歷,都能反映並折射出時代的進退脈動。」
本書的主要內容是敘述和反思自上世紀 80 年代後期至新世紀初期中國大陸思想文化空間中的種種學說、活動,以及產生這些學說、活動的社會原因和心理動機。
中國大陸的民間社會在此期間開始萌芽發展,思想文化上的種種言說與活動反映了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而來的生機與陣痛。
作者以親身經歷,敘述意外入獄與和獄中員警鬥志博弈的全過程。近年中國經常發生的抓捕和監禁,表明了中國社會生活特徵和趨勢;這個特徵和趨勢是──中國日益法西斯化,中國正在變成一個員警國家。
作者不斷發出中國正在變成員警國家的警告。這話並不是空泛的譴責,而是對中國社會生活中一個顯著特徵的概括:員警無處不在,遇到問題都靠員警抓人解決。
這是一個關於個體經歷的故事,透過深刻觀察中國社會特徵和趨勢,呼應著民主自由的未知,以及沉重的無奈。
本書特色
1.作者徐友漁因六四紀念研討會意外被捕,突如其來的入獄影響了他的研究與治學方向,揭示了中國社會日益法西斯化的特徵和趨勢,審訊員警之間的博弈展現了在當今中國法治原則受到挑戰時的踐踏和捍衛。
2.本書不僅呈現了「議題犯」獄中生活的困難,以及回歸自由後面臨的限制,更希望透過這本書提醒讀者關注中國的法治、人權和自由現狀,反思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徐友漁
1947年生於四川成都。
1977年進入四川師範大學數學系學習,1979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哲學系,1982年取得哲學碩士學位並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直至2008年退休。
曾在牛津大學、哈佛大學等學校從事訪問研究,並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日本北海道大學與美國紐約新學院大學擔任訪問教授。
學術研究集中於語言分析哲學、政治哲學、當代中國社會思潮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獲2014年度奧洛夫‧帕爾梅獎。
目錄
前言
第 一 章 劫後餘生:成為文革後中國首批大學生
第 二 章 我為什麼要研究分析哲學
第 三 章 牛津大學的氛圍
第 四 章 80年代「文化熱」的榮景與脈絡
第 五 章 我與「六四」
第 六 章 90年代:場景大變換
第 七 章 自由主義、新左派、社會民主主義
第 八 章 我的文化大革命研究
第 九 章 在瑞典與帕爾梅結緣
第 十 章 劉曉波、零八憲章與諾貝爾和平獎
第十一章 我愛台灣
第十二章 員警如影隨形
第十三章 六四周年紀念研討會
第十四章 在看守所
序
前言
德國著名哲學家狄奧多.阿多諾(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有一句名言:「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也是不可能的。」這句話對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詮釋。
我是以最淺白和直接的意義來理解並踐行這句話──自從經歷了1989年六月四日凌晨發生於北京的那場殘暴鎮壓和血腥屠殺之後,我再也無法以身為一個書齋學者而滿足,今後我所有的研究、思考、寫作,都必須與正在改變的中國現狀相關,必須和追求自由、民主、法治的目標相關。
1988年夏天——距六四事件發生不到一年──我自英國牛津大學返回北京,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從事當代西方哲學的研究工作。那時的我,心態真可用「春風得意、躊躇滿志」來形容。當時,我被視為「牛津學成歸來的學子」、「世界知名哲學家達米特(Michael Anthony Eardley Dummett)的弟子」,被學界前輩和同道寄予厚望;歸國不久,我通過了特殊的考試和成果評議,破格晉升為副研究員,成為本所最年輕的具有高級職稱的科研人員;此外,我還是當時國內頗具影響力的民間學術文化團體《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的核心成員。也就是說,不論在體制內還是體制外,我都被視為是大有前途的。
然而,六四事件改變了成千上萬人的生活方向,我的改變是內在的。我對個人在體制內的提升與發展全然失去了興趣與動力。我研究哲學的本意是為了使國人的思維更科學、更理性、更精確,面對社會上迫切的現實問題,繼續研究語言分析哲學有點像是關在象牙塔中作詩,顯得太高雅奢侈了點;因此我作出調整,轉向研究與政治社會更為直接相關的領域。
進入90年代之後,中國大陸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和社會心理各方面均呈現出與 80 年代完全不同的面貌。在中共黨內,對於經濟體制改革的反對聲浪暫時平息,但貪腐、錢權交易、化公為私等亂象令人觸目驚心;與 80 年代社會以科學、民主、啟蒙的思想為主旋律大不相同,知識界內對科學民主的質疑和對啟蒙的攻擊日漸甚囂塵上。
中國社會現實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對有責任心的思想者提出了挑戰,我必須回應這些挑戰,而不能繼續沈溺於抽象的形而上學理之中。因此,我治學方向的轉變不但是一項道義上的命令,而且是正合其時的明智選擇。
要完成從學院派知識分子到公共知識分子的轉變,對我並不困難,因為在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和許多青年學生一樣,經歷了一場以筆為武器,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鍛煉。「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尚存於身,對時局的敏感沒有絲毫減損。但是,如何在做學問的同時表達社會關懷,我仍然面臨一些可能和選擇。
首先的考慮是告別學術,專心致志於社會批評,以匡正時弊為自己的專業,還是一邊從事學術研究,一邊著力於社會關懷?我選擇了後者而不是前者。其次,取代語言分析哲學,我要以什麼學科為自己的新專業?是與政治、社會直接相關的政治學、社會學?這樣轉彎太大,也不太投合自己的興趣;幾經反覆思量,我的選擇是在思辨和理論層面從事一種與政治、社會評論有關的專門學問,使自己在現實層面的社會評論有更深厚的學理資源支撐,並使二者相得益彰。
為此,我告別了苦心鑽研多年的語言分析哲學,轉向政治哲學。我花大力氣攻讀當代政治哲學的經典著作,並發表一系列專題學術論文,我的社會評論偏重於公平、正義、平等、個人權利和法治層面。這個轉向對我而言並不太難,也不完全出自實用,因為我本來就對政治哲學有莫大的興趣,並在這門學問中不斷獲得靈感和啟示。
本書的主要內容是敘述和反思自上世紀 80 年代後期至新世紀初期中國大陸思想文化空間中的種種學說、活動,以及產生這些學說、活動的社會原因和心理動機。我相信,這一時段將在未來書寫的中國歷史上占據特殊地位:中國大陸的民間社會在此期間開始萌芽發展,思想文化上的種種言說與活動反映了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而來的生機與陣痛。這一段時間很特殊,在這之前,中國只有黨文化和黨的意識形態;在這之後,隨著「定於一尊」、「七不講」局面的形成,民間話語空間日漸萎縮,幾近為零。近代以來,中國的自由、民主、啟蒙話語總是剛萌芽就夭折,今後中國的自由民主話語空間開闊發達之時,很多東西還得從中斷的地方講起。
我帶著一種雙重身分的自覺參加這一段歷史時期的言說活動中,一方面,我自命為思想史家,力求全面觀察、客觀記錄、大力介紹這一時段的思想交鋒和思潮流變,了解其生成的背景,判斷其社會影響力;另一方面,我作為思想者和言說者,積極伸張和捍衛某些立場觀點,反對和批駁某些主張與看法,在某些爭論中充當某個派別的發言人。
我盡量避免這兩種身分合一的弊端和衝突,以免陷得太深而產生意氣偏頗。然而我卻反倒常常感覺到這兩種角色的增益作用。讓我最有感觸的是──只有問題中人才能對問題有透徹的理解,只有身處某個派別才能對此派及對立派的主張有深刻認識,避免貌似的公允、面面俱到的表面文章。在這個問題上,我能體會法國著名思想家雷蒙.阿隆(Raymond Claude Ferdinand Aron)對自己身份定位中暗含的褒義,他在自傳中自稱為「入戲的觀眾」(中國大陸譯為「介入的旁觀者」)。
我深知,相比於滾滾歷史巨流,我所發出的聲音實在是微不足道,甚至整個知識界的喧嘩爭鳴也可能被後人視為杯水風波而已;但我想強調,某些個人的努力與經歷,還是能夠反映並折射出時代的進退脈動,個人經歷的豐富性與生動性,構成了歷史這個宏大故事的具體細節,品味這些細節,將有助於體悟歷史走向和時代風雲。
我對中國大陸的現實狀況作了大量的分析與批評,令我感到高興的是,讀者們歡迎並欣賞我的立場與觀點,是基於這兩大特色:一是理性,二是建設性。我很滿意這樣的反饋,因為理性和建設性,正是我所追求與彰顯的,我認為我對這樣的讚譽當之無愧。
但是,大約從進入新世紀起,我的著作就無法在中國大陸發行,從2014年夏,在大陸的報刊、媒體(包括網絡)上就再也看不到我文章的蹤影。當局打壓的原因從不言明,我想一是我不迴避與劉曉波等異議人士的交往,二是我一直公開呼籲當局採取寬容政策。最後,各種打壓終於達到頂點── 2014年5月5日,我被北京市警方傳喚,6 日起轉為拘捕,關押於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解釋「我究竟為何被捕」不僅關乎我個人的聲譽和利害得失,我將在本書中詳細講述事情的來龍去脈。簡單來說,情況就是:一群北京市民在一個私宅中舉行六四事件紀念研討會,我因身為會議的發起者和組織者之一而被捕。然而事情的實質是──中國已經淪落為員警國家,我被抓捕不是因為犯了法,而是國家的執法者公然違法。
抓捕我的罪名是「尋釁滋事」,對於像我這樣一個成天足不出戶、伏案寫作的教授而言,捏造這樣的罪名真是不知羞恥!我在本書中詳細記述了我與審訊員警之間的博弈,那是一場踐踏和捍衛法治原則的較量。
和最近一、二十年中經常發生的抓捕和監禁相比,我的案子並不突出,但是,它同樣表明了中國社會生活特徵和趨勢;這個特徵和趨勢是──中國日益法西斯化,中國正在變成一個員警國家。當 2008 年奧運會在北京舉辦之時,我就將其與 1936 年的柏林奧運會相提並論,在這之後,我不斷發出中國正在變成員警國家的警告。我說這話並不是空泛的譴責,而是對中國社會生活中一個顯著特徵的概括:員警無處不在,遇到問題都靠員警抓人解決。
中國目前距憲政和法治的目標還很遙遠,而且近年來的趨勢是每況愈下,但我從生活經驗和歷史研究中得知,這個目標遲早總會在中國實現;我堅信,總有一天,中國會變為一個文明的國度。
此前言完成於 2022年5月6日,正好是我被關押於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8 周年的紀念日。
徐友漁
Collapsible tab
Add additional product informations